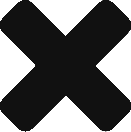Nov 23, 2016
Jerry Yang
對訴訟的恐懼,使人們錯過一個個試圖理解彼此的機會,偏見、歧視等想法只能藏在腦中躁動著,等待任何能讓自己大聲講出偏見的代言人。而今天那個代言人剛好是川普。
當年搬到矽谷時,於公於私都花了一點時間才適應。
在生活上,從出生開始住了三十幾年的城市,一下子搬到我們透過電視影集和電影所熟知的、所謂「美國夢」的市郊(sub-urb),不管是公共交通的匱乏,購物中心(Shopping Center)的大量消費習慣,餐廳服務水準的小費導向,飲食文化的重量不重質,甚至連晴朗天氣的一成不變,都讓我花了好些時間才適應。
工作上,以執行業務來說倒是沒有太大的改變。當年無線網路晶片組雙龍頭之一的Atheros一直都有很棒的全球研發環境,從台灣搬到矽谷也只不過就是時區換了,可樂免費喝到飽,一直只在電郵和視訊交流的矽谷同事們突然間變成真人版——「哇!我不知道你原來有 190 公分高!」——等,要不然工作方式和內容其實一樣。
唯一有個很大的差別,事後看來那不但是我最終離開矽谷(乃至於美國)的原因之一,也是這次讓人震驚的美國大選的根本病兆之一。
打從一開始,在跟同事吃午餐和閒聊中,我很快被告知一個新的潛規則:在職場要避免聊政治、性別、宗教、種族、性傾向等相關議題。
沒在美國工作過的人可能會以為這是為了避免歧視言論出現,以保護矽谷各色人種的平等。但這種看法也可以說是對,也可以說是不對。
打開天窗說亮話:這樣的潛規則其實最主要是讓大家能夠避免訴訟,而且更進一步地保護公司不會因為員工的歧視言論而被告。而且比起前者來說,後者的重要性更高,有些矽谷公司甚至把「在辦公場所禁止聊政治、性別、宗教、種族、性傾向等相關議題」這樣的規定放入公司員工章程中。
有些人可能會有疑問:員工自己嘴巴賤,愛講爭議性話題,導致擦槍走火,引起訴訟,甘公司啥事?最少台灣的大老闆們絕對無法理解這樣的事情。
要了解這一點,只要回想一下知名的「老太太自己不小心被麥當勞咖啡燙到」的訴訟事件,就應該可以恍然大悟。
美國是判例法結構,相較於大陸法系嚴定法律和罰則,判例法則是根據法庭上的辯論決定賠償金額。判例法的好處是彈性高,能隨著時代進步,而且能透過「懲罰性賠償」這個工具,去誘使敗訴者和與其他有著類似問題的人或機構主動趨向合理合法的行為。
但在這種體系下訴訟也可以從很惡劣的角度出現。以職場來說,因為告公司永遠比告個人有機會得到更高金額的賠償——只要律師能夠成功說服法官或者陪審團——因此大多數可能引起訴訟的職場個人行為,在某些嗜血的律師眼中都可以用「容許一個 XXX 的職場環境,導致我的客戶受到 OOO 傷害」的訴求去控告公司法人,而非引發爭議的自然人。
舉例來說,假設當年我在職場上午餐閒聊的空檔,用滴水不漏的政策和哲學分析批評共和黨,導致支持共和黨的某位同事精神創傷,看到我就會不住作嘔無法工作,最終被公司開除。比起直接告我,他的律師可以改告公司「容許一個讓員工可以用政治議題精神迫害其他員工的職場環境」,然後主張這樣「被容許」的環境可能造成不只一位、而是將近一半的員工總數(支持共和黨的那一半)精神創傷,為了避免這樣的事情,應該追加「懲罰性賠償」等等。
簡單來說:美國是一個以對於訴訟的恐懼壓迫公民實現政治正確性的國家,這裡的工具百分之百是鞭子,不是胡蘿蔔。
這並不是說他們沒有透過教育或者辯論去引導公民在思想上進步,但扣除臨海各州(coastal states)和公立學校體系,大部分的學校並沒有誘因也沒有義務,去循循善誘年輕人做辯證並長成為完整獨立思考的公民,更不用說那些嬰兒潮世代,沒有受過現代三級教育的白人們。
因此這幾十年來美國在平等議題上的進步,其實對很多白人、男人和異性戀來說是一種「政治正確的白色恐怖」,懸吊在他們頭上的不是理性的責難,而是可能的鉅額賠償。
「我不同意你,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伏爾泰這樣說。
但如果因為恐懼訴訟,連說都不能說,連討論都不能討論,大家就會把自己的偏見藏在心中豢養著,越養越肥。每一次看到正派媒體抨擊自己其實也有的那個偏見,不公平感就更深,心理上也就更佳捍衛自己的偏見,願意接受任何能夠支持自己偏見的「事實」——不管這「事實」是不是福斯電視網那種「事實」——以及任何能夠幫自己大聲講出偏見的代言人。
只是今天那個代言人剛好是川普而已。
在我生活於矽谷的那幾年,儘管加州已經是美國數一數二的自由派,矽谷更是有色人種數量遠高於白人的一個環境——在當年我部門位於聖塔克拉拉的五十位左右同事中,只有三位稱得上是美國白人——但在生活中,不管是和汽車銷售員討論,或者在星巴克點咖啡,乃至於尋找出租公寓的過程中,我還是會注意到一些明明已經到了最邊、但被硬吞回去的可能會形成歧視的言論,往往我就看著對方打斷自己的說話節奏,笑著轉換話題。
回想起來,每一個這樣的時刻,我們都錯過了一個可以真心交談、試圖理解彼此的機會。
戰後出身斯洛伐尼亞、擅長心理分析的當代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 1949-),曾經對於政治正確性有著強烈的批評。
他當然不是一個歧視者,但他認為政治正確性只不過是另一個社會威權工具,強迫大家對於各種無法避免的先天或後天的不平等「視而不談」。更糟的是,它成為一種隱性的行為控制——就像美國的訴訟威嚇——而不是讓公民透過辯論去進化,去從打從心裡的接受差異和追求平等。
在他這個訪談中,他舉了個非常有說服力的例子:一個父親要小孩犧牲週末遊玩的時間,去鄉下拜訪祖母。
如果這個父親是威權的父親,直接下命令要求小孩去拜訪祖母,那麼最少這是一個可見的、明確的威權,是可以反抗的。
但如果父親說:「你知道的,我無法強迫你去拜訪祖母,但她這麼愛你疼你,去看她是個好事。總之,看你自己決定囉!」突然間這變成一個社會壓力,而且是沒有威權對象可以反抗的,小孩只能夠吞下所有心理上的不滿和壓力,自己做出決定,不管最後是去還不去,都已經在心靈上留下一個包袱。
我仔細咀嚼著齊澤克教授深入淺出的分析,回想著在矽谷生活時那些我們錯過的寶貴溝通時刻,看著現在電視上那讓人作噁的金髮橘臉,環顧四周巴黎咖啡座裡交換的那些沒有惡意的玩笑,和走在聖日爾曼大街上談笑風生的黑白情侶,深深地慶幸自己在四年半前做出了一般人不會做的選擇,離開矽谷來到巴黎。
明年換我們了。不管是左傾右傾,我們將針對各種議題高聲辯論得面紅耳赤,甚至大打出手,然後不論結論為何,我們都將攜手阻止瑪琳・勒潘成為下一任法國總統。
【本文獲 Jerry Yang 授權刊登,未經原作者同意,不得轉載。原文出處 楊建銘專欄:川普、矽谷與政治正確性,風傳媒】Photo credit: 美聯社
只要註冊為用戶,即可隨時掌握最新的社群活動及職缺相關資訊。歡迎至 https://meet.jobs/sign-up 註冊為用戶。更多討論與交流,歡迎加入我們的臉書社團「Meet.jobs 全球職場情報交換中心」
作者介紹
Jerry Yang
畢業於台灣大學電機系,在台灣、矽谷和巴黎從事 IC 設計超過十年,包含創業四年。在巴黎工作期間於 HEC Paris 取得MBA學位,轉進風險投資領域,現為創投基金 Hardware Club 合夥人。www.jmyang.com